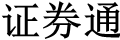[申能股份]CCER重启:利好政策频出,买卖双方还有这些难处
1月下旬,一則“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市場正式啓動”的消息引爆了鄭江灼的朋友圈。何時能夠繼續暫緩了六年多的CCER(全國溫室氣體核證自願減排量)備案申請工作,再度成爲他和碳交易行業同仁探討的焦點。
我國CCER市場於2012年開啓。2017年,國家發改委暫緩受理了CCER的備案申請。2023年10月,生態環境部發布《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管理辦法(試行)》,這是保障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市場有序運行的基礎性制度。隨後,生態環境部發布第一批CCER方法學,分別爲造林碳匯、併網光熱發電、併網海上風力發電和紅樹林營造。
多位行業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前CCER的備案簽發工作仍未正式啓動,目前交易對象也僅限於2017年前批准的存量項目。不過,有關部門陸續搭建起的基礎性制度和承載新增項目的交易平臺體系,讓業界普遍認爲重啓的“鐘聲”越來越近了。
“最近我們接到了很多客戶的諮詢,大家都感覺到距離重啓備案不遠了。很多交易員和業主已經編好了申請材料,準備重啓後爭取第一時間遞出去。”多年從事碳交易諮詢工作的鄭江灼說。
1月31日,中國銀河發佈研報稱,預計2024/2030年碳交易覆蓋額爲60億噸/106億噸,碳價爲74元/139元。按照5%抵消比例測算,2024/2030年對應CCER市場規模爲224億元/735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抵消比例存在上限、核證方法過於複雜等問題曾經長期制約着CCER市場大面積普及。即便重啓以後,這些因素是否會讓投資者對CCER重新燃起的熱情逐漸熄滅,數百億規模的市場能否兌現,在一些從業者的心中仍然要打問號。
變化中的CCER市場,並非簡單重啓
從無到有,從過去的供大於求到如今稀缺的“香餑餑”,CCER的定位隨之變化。
德國智庫機構阿德菲(adelphi)碳市場專家陳志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12年是我國CCER市場起步的關鍵之年。此前,中國企業主要通過CDM(清潔發展機制)參與國際碳市場。但是,隨着歐洲碳市場改革以及京都協議書第一階段的結束,CER(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量)價格不斷下跌,CDM項目發展受阻。於是,我國開始籌建國內自願減排碳交易市場。2012年CCER進入交易階段。五年後,CCER項目備案暫停,只有存量CCER在各地方市場中交易。
根據國家發改委2017年發佈的公告,“暫緩申請受理”CCER是因爲存在“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量小、個別項目不夠規範等問題”。
到了2023年下半年,CCER備案重啓的準備動作頻出。2023年10月,生態環境部先後發佈《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管理辦法(試行)》、《關於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市場有關工作事項安排的通告》以及首批四個方法學。2024年1月19日,國家認監委發佈《關於開展第一批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項目審定與減排量覈查機構資質審批的公告》,將開展第一批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項目審定與減排量覈查機構資質審批工作。2024年1月22日,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市場啓動儀式在北京舉行。
“這次交易啓動不是簡單的‘重啓’,應該說是啓動了新的體系。因爲歷史背景不同、主管部門不同,核心要素也都不同了。”美國環保協會北京代表處碳市場主任劉洪銘對第一財經記者強調。
劉洪銘分析,舊CCER體系的建立背景是後京都議定書時期,爲了繼續鼓勵曾經在CDM機制下蓬勃發展的中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行動而設定。而新CCER體系是巴黎協定時期中國爲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和實現氣候目標、推動更廣範圍減排和市場機制建設的新需求,除了主管部門由國家發改委轉爲生態環境部之外,管理辦法、系統、方法學等也都是新的。
在新出臺的管理辦法中,明確表示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及相關活動將會推動我國實現碳達峯碳中和目標,且新的全國自願減排交易市場與全國強制碳交易市場一起形成了完整的全國碳市場體系。“這些職能都是之前舊CCER項目所不具備的。”劉洪銘稱。
“謹慎的樂觀”,業界盼建好基礎設施
頻繁的重啓準備動作,讓各路機構看到“利好”,近期一些金融機構也上調了相關公司的評級。與此同時,許多碳交易行業資深人士對此卻抱以“謹慎的樂觀”,態度更爲保守。
鄭江灼告訴記者,從當前全國碳市場和CCER的交易行情來看,往往到了臨近履約週期的後半年,市場纔會逐漸活躍。大多數時間裏,控排企業的“惜售”心理嚴重。一方面,這是因爲有的企業缺乏專業的碳資產管理隊伍,對於履約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目前碳市場尚未放開機構投資者的參與,有的企業寄希望於最後的履約節點出售,以此獲得更豐厚的收益。
“雖然全國碳市場啓動到現在,已經過去兩年多了,但是很多的民營企業乃至央國企,對於自身的碳資產、每年的排放和配額數據極少能掌握得及時且精準。根據現行的政策,次年的年中到年底,纔會發佈上一年的碳配額分配方案,企業對於當年的排放量是富餘了還是有缺口,心裏沒數,也就不敢提前交易。”鄭江灼說。
當前的碳市場缺乏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發現價格的功能。與此同時,“魚龍混雜”的碳交易行業,有時也會加深外界對於某些項目開發門檻的“誤解”,過度放大預期。
“我見到過挺多不專業的市場參與者,主動向林業主管部門以及林權所有者宣傳可開發的CCER的價值,動輒就是測算出了上千萬元的經濟價值,實際上遠遠沒有這麼多。”鄭江灼表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經常把“林業碳匯”和“一片林子能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氣”兩個概念劃上等號,而現實中,經過核證的林業碳匯要在後者的前提下滿足“新造林”等多重要求。
多位行業人士告訴記者,當前,無論是CCER的“買方”還是“賣方”,雙方都經常在交易中感到一些爲難之處。
以建築業爲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終端能源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產業之一。根據中國建築節能協會等發佈的《2023中國建築與城市基礎設施碳排放研究報告》,當考慮基礎設施時,全國建築業全過程碳排放總量爲50.1億噸二氧化碳,佔全國能源相關碳排放的比重爲47.1%。
友綠CEO、中國建築節能協會低碳健康地產專業委員會祕書長黃俊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產業鏈角度而言,目前企業的積極性普遍不高,其中核證成本過高是不可忽視的一大因素。
“三年前,我們曾經給國內某家知名民營房地產商做過碳盤查工作,因爲其‘三恆’的科技系統能效優勢非常明顯,四十多棟建築每年減排總量達到4.4萬噸,但單棟建築物減排量僅爲一千多噸。按照CCER六十元每噸的價格,對應的收益是六萬多元。但是,爲了得到這筆收益,僅開發和核證就要額外花費數十萬元,經濟上完全不划算。”黃俊鵬稱。
在黃俊鵬看來,成本遠高於收益是影響相關企業減碳熱情的主要因素。他建議,對於處在特殊時期的地產及產業鏈企業,一方面,有關項目可採用區塊鏈等新技術,在確保數據可溯源的基礎上,降低核證費用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將建築資產的金融屬性與低碳屬性相結合,通過制度設計,根據“建築碳信用”實施不同程度的金融優惠政策,激勵企業持續減碳。
“在發展CCER的過程中,很關鍵的一點是,我們需要注重的是項目和減排量的質量,而不是一味追求‘規模’。”劉洪銘對記者表示,隨着技術的不斷髮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切實需要,未來還會出現一些新的更具有潛力的自願減排領域,特別是新技術開始運用的初期往往都是高成本的,這也是碳市場能夠幫助引導氣候投融資推動低碳技術發展的地方,但無論如何都需要保證高質量。
幫企客致力於爲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財經資訊,想瞭解更多行業動態,歡迎關注本站。推荐阅读
-
阳煤化工是氢动力股吗(美国加息时间)
财经常识的学习以及使用需求重视市场剖析才能的晋升。投资者们需求具有对市场趋向以及行业静态的敏锐洞察力,以掌握投资机会。长话短说,如...
-
羚锐制药股票资金流向—羚锐制药股价几何(贵州燃气)
股票投资是一种需求耐烦以及毅力的投资形式,投资者需求有久远的投资目光以及正确的投资战略,能力正在市场中取得长时间的稳固报答。接上去...
-
000835基金昔日净值查问、000831基金明天净值走势图(今日证券行情)
股票市场是一个充溢机会微风险之处,天天都无数以万计的股票正在买卖。关于投资者来讲,抉择一只好的股票长短常首要的,由于这关系到他们的...
-
「603507」易成新能300080股票行情
本文提供了如下多个解答,欢送浏览:1、引言:新动力行业的灿烂新星2、业绩体现:持重增进面前的驱能源3、市场存眷焦点:政策导向与市场...
-
「570008」002468申通股分重组是啥
正在以后的经济情势下,财经常识的首要性显而易见。理解经济情势、政策变动、市场趋向等方面的信息,能够协助投资者更好地制订投资战略,掌...
-
期货k线图
期货K线图是期货买卖市场中十分首要的技巧剖析对象,经过察看K线图能够协助买卖者判别市场走势,制订买卖战略。那末,期货K线图到底怎样...
-
002318股吧交银前锋基金估值
股票市场是一个高度竞争以及变动的市场,投资者需求时辰放弃警惕,实时把握市场静态以及公司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议计划。明天本小站...
-
002825纳尔股分中国加入msci最新消息股票最新音讯.002825纳尔股票行情
股票投资是一种需求耐烦以及毅力的投资形式,投资者需求有久远的投资目光以及正确的投资战略,能力正在市场中取得长时间的稳固报答。接上去...
-
(002221股票)英科医疗股票股吧、英科医疗能否值患上临时持有
股票市场是一个高度竞争以及变动的市场,投资者需求时辰放弃警惕,实时把握市场静态以及公司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议计划。明天本小站...
-
安纳达股票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是公募仍是私募
正在以后的经济环境下,财经常识的首要性一直晋升。投资者们需求理解微观经济情势、行业静态、公司财政等方面的信息,以更好地掌握投资机会...